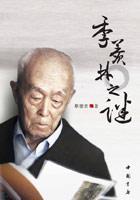|
|
蔡德贵:季羡林学吐火罗文之谜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0日15:19 新浪博客
蔡德贵:现在全世界真正读懂全世界不超过7、8个人。 精彩语录: 在德国读大时有一天季羡林在选课表上偶然看见梵文、巴利文两门课程,这时他忽然找到了感觉,这正是自己在清华大学想跟着陈寅恪先生学而没有学到,而居然在这里找到,就下定决心跟着瓦尔德施米特学巴利文。 季羡林留德前的一段尴尬日子 主持人:从中学老师后来怎么去的德国,后来怎么又回来? 蔡德贵:刚才提到宋繁吾先生来主要不是让他教课,是为了让他的帮派斗争服务,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北大派,一派是北师大派,北大派是宋繁吾,北师大派是另外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在那里领着,两派势均力敌,宋繁吾为了维护北大派的威严,需要借助力量,如果调一个北大派的人来就太明显了,就想到季羡林,清华毕业的,不是北大帮,但是济南高中的学生,让他来壮大我的势力,一来交代任务。季羡林,你给我组织一个高中校友会,你来当主席,季羡林读不懂这句话,不知道当主席是干什么,校友会组织起来,但是没有帮宋先生的忙。 第一学期过去了,宋繁吾先生给他有三个字的结论:太安静。没读懂我的意思。这时他同屋住的一个河南籍的老师偶然一问,你拿到了没有。拿到什么呢?下学期的聘书。那个河南籍的教师下学期的聘书没拿到,等于下学期没有位子了,卷铺盖走路了。但是过了几天季羡林下一学期的聘书来了,这样第二学期的教学任务他心里有了底了,但是开学以后没有多长时间,明显感觉到宋繁吾对他越来越冷淡。因为让他帮忙没帮上,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下一步打算还找不着对策的时候,这时听到清华大学冯友兰文学院长和德国的大学签定了一个交换留学生的协定,他报了名,结果被录取了。这样他就有了机会去德国留学了。所以,他后来和乔冠华、王竹溪很多后来大文明家坐着同一列车到了德国。 主持人:有关季老的履历或者是大学之前这一段经历真的听了您的介绍,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有感触,特别受震动,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而且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说到这儿,您刚才也举例了,其实季老师的一生中遇到很多郝老师,这些郝老师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哪位? 蔡德贵: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决定他以后一生的研究方向。高中部的王昆玉先生、董秋芳先生,包括王树鹏校长、胡也频,对他影响都很大,他一生都不忘。而且从他那儿,高中部他已经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古文字的基础,写一手很好的文言文。 季羡林到底学习过多少种语言 主持人:其实说到季羡林老师的文字功底不得不提,因为季老研究的有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都是绝学,很少有能知道的,季老为什么要选择大家都很少知道的这种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另外,您在书中也提到过吐火罗文之谜,这又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说一下。 蔡德贵:因为他选择了清华,考上大学以后,北大、清华都考上了,选择清华的目的就是觉得清华大学留学容易,但是毕业之后没有实现,回去又教了一年高中,又通过冯友兰院长和德国签定的协定,他有机会去德国留学了。这个时候他到德国的时候碰了一个大钉子,这个钉子是什么呢?在清华大学他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德国语言专门化专业,就是学德语的,但是到了柏林,和交换处的一个女职员对话,德文既听不懂又不会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清华大学的德语教学用英语教的,咱们现在都设想不出来。学生要求用德语教,老师很快地说了几句德语,问学生听懂了吗?学生当然听不懂,说你们既然听不懂还是用英语教的,所以四年的德语这门课是用英语教的,季先生的学术毕业论文也是用英语写的。到了德国之后,和交换处这么一交流,听不懂、说不出,人家感到很奇怪,你德语专门化怎么专门化的?没有办法,你们必须进加强班。他跟乔冠华两个人就被安排到柏林大学进德语专门强化班培训了半年,把口语过关了。这时面临着选择专业。季羡林下决心绝不学和中国学沾边的学问,我不能到德国来读中国的东西,不能到这儿来读老子,这时决心一定,但是很长时间里边他找不着自己的方向。因为他后来选了哥廷根大学,进了哥廷根大学一看,这些专业都没有自己感兴趣,有半年时间他选了拉丁语学了一段,希腊语学了一段,各种语言他几乎都有浅尝辄止的经历。 大概过去了半年,他在教务处门口看到了一张表,上边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位年轻的教授36岁,叫瓦尔德施米特,他开的语言是印度语言,其中就有梵文、巴利文,这时他忽然找到了感觉,这正是自己在清华大学想跟着陈寅恪先生学而没有学到,而居然在这里找到,就下定决心跟着瓦尔德施米特学巴利文,瓦尔特施米特的作为刚刚升值为教授的年轻教授,接收了他唯一一个学生。 季羡林的“吐火罗文之谜” 主持人:梵文和巴利文的基础是在德国打下的。您说到的吐火罗文是怎么样的文字?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 蔡德贵:吐火罗文实际上本来不是季羡林先生计划当中学的语言,但是后来二战爆发以后,瓦尔德·施米特是年轻教授,他被征从军,上战场了,这时季羡林先生准备跟着他读博士论文,而且瓦尔德·施米特帮助他确定了一个论文的题目,从语言语尾的现象谈的一篇博士论文,题目选定之后,瓦尔特·施米特就上了战场,这时季羡林先生用了一年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非常细心、非常用功写了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的导言,就是引言部分,自己非常得意,觉得应该会成为传世之作。 在这个时候瓦尔德施米特从战场上回来探亲,大概半个月的假,一看老师回来了,双手端着这篇导言给瓦尔德·施米特老师送过去。老师拿过来以后看了一眼说先放在这儿我看一看,看完了再还给你。过了一个星期叫老师把季羡林叫过去了,把这个论文就还给季羡林,季羡林拿回来一看,论文上边一个字没改,问老师怎么回事,老师说你仔细看,后来仔细一看这个论文导言最前边的一个字有一个用铅笔画的圆括号,然后论文的最后一页,句号后边一个铅笔划的圆括号,他不理解,又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老师我不懂。老师说什么意思?统统不要。季羡林如五雷轰顶,一年时间查阅那么多资料居然统统不要,老师接着非常耐心地跟他说,你这篇论文下的功夫非常大,用的资料非常丰富,好多资料你用的都很准确,但是有一点,你季羡林自己的特点没有。这样的一篇导言假如提交给答辩委员会,不管哪个答辩委员,从哪一个角度来攻击你,都会把你置于死地,因为没有你自己的话,统统不要。 这五雷轰顶以后季羡林一反思,老师说得对,后来这篇论文全部是新观点,到答辩的时候,几位答辩委员异口同声。这是后话了。 但是因为老师被征从军,季羡林那个时候在哥廷根大学已经小有名气了,这么勤奋的学生很难得,谁不想要一个好学生。这时出来一个8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教授,叫希克,他趁着瓦尔德施米特从军把季羡林叫过来,说我要教你一门绝活。季羡林说我脑子里已经装了7、8种语言了,别再让我学语言了,老教授说我就让你学语言,把要我最绝的绝活传给你,别人我不传,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80多岁的老先生,季羡林拧不过他,硬着头皮接,学吧,结果一学才知道,这门学问叫吐火罗文,是中国新疆地区中世纪焉耆这个地方的古文字,当时全世界读懂的不超过30年,而希克教授和另外一位教授是花了30年时间编了一本吐火罗文辞典,看好季羡林先生可以培养,非要教给他,这样季羡林在被迫之下学了这门吐火罗文,而且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语言。 主持人:也是一门绝学。 蔡德贵:现在说能够真正读懂全世界不超过7、8个人。
【发表评论】
|
||||